復旦大學邯鄲校區在哪;復旦大學邯鄲校區在哪個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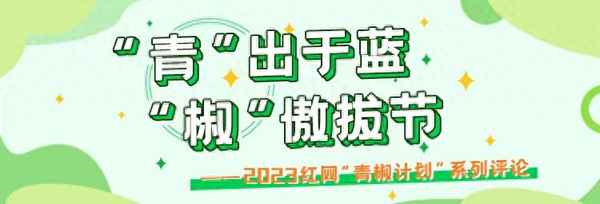
□葉晴朗(南京大學)
當前,大學校園疫情后的“解封”已是現在進行時。據極目新聞報道,5月20日,復旦大學邯鄲校區開放了校外人士預約入校的線上渠道,上海師范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的校園也已逐步恢復對公眾的開放。
不過,輿論場上對校園是否應該開放的意見仍存在很大分歧:支持開放,或反對開放。早在五一期間,有關“深大是誰的”“深大是國家的而不對外”的爭論就曾引發廣泛討論。
實際上,自今年年初新冠被列入“乙類乙管”后,關于大學校園是否應該重新向社會開放的問題就一直處在爭論之中。反對者質疑校園放開后存在的治安隱患,學校正常教學秩序、科研環境、校園氛圍都會受到影響;而支持者則認為校園應該回到疫情前的開放狀態中去,并且從大學精神、大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等角度駁斥封閉論者的觀點。
討論看似激烈,實則殊途同歸。與其說兩種觀點是在爭論“校園是否應該開放”,不如說是在探討“校園應如何開放”。
從封閉論者的觀點來看,他們擔心的秩序、校園資源等問題本質上是校內設施開放策略、保衛部門工作質量等高校校園管理水平的考量,而非開放與否的問題。開放論者要求“回到疫情前”,而三年前的中國高校其實并非簡單的、徹底的“開放”,不同院校根據其具體情況,也會有不同的管理策略。
改革開放后,除了SARS疫情期間,國內最早進行校門進出管理的院校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2008年后,由于旅游客流量大增,清北兩所高校作為國內知名度最高的校園,在教學、科研工作之外,龐大的人流量使其不得不承擔起旅游景點的職責。有限的校園管理水平難以應對,才不得已開始進行入校身份驗證。同為知名景點的蘇州大學管控更為嚴格,必須出示校園卡才可以入校;廈門大學則采用“景點開放式”的策略,需要出示身份證明,在規定時間段內可以進入思明校區,其他校區的教學、科研設施則不對外開放。
來訪游客相對較少的高校則往往不設限制。例如,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訪客多為周邊居民,客流量有限,因此長期不設門禁。2018年,該校區試行門禁引起爭議,幾周后又取消了門禁。可以說,中國高校在2008年后的校園開放采用的是“總體開放,部分管控”的策略,既不是徹底的開放,更不是完全的封閉。
新冠肺炎疫情后,校園從三年的封閉中恢復開放,事實上已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今年2月,央視網發布了名為《大學校門,該打開了》的評論文章,認為大學不能對封閉帶來的管理便利產生依賴,要求將校園開放提上日程。根據南大校媒《新潮》的統計,截至4月30日,清北均已開啟社會人士的線上預約入校渠道,人大、東南大學等高校也開放了校友入校、校內聯系人等入校渠道。5月16日,南京大學保衛處發布公告稱,南大將在線上預約來訪渠道之外設立校園開放日,在校慶、畢業季等特殊時段向社會直接開放。在整體開放的背景下,各個高校也正在探索合理的、符合本校具體情況的、適應于當前高校管理水平的開放路徑。
應該明確的是,高校校園開放之所以在近十年成為廣受關注的公共議題,根本上是源于社會公眾對高校校園的向往,是大學與社會聯系日益密切的體現。向往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客流量的迅速增長,而當這與發展相對較慢的校園管理水平產生沖突時,校門管控的加強也就成為了不得不采取的應對措施。一方面,我們應該充分理解高校管理上的困難;但另一方面,高校也應積極探索精細化的校園管理模式,為更有序、更高水平的開放提供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們也看到全國各地的高校都在漸進地摸索校園開放之路,在走向開放的大前提下,這首先是值得鼓勵的。至于如何在校園秩序、師生安全與開放需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則是對每一個高校管理部門的考驗。我們相信,隨著管理水平的提高,高校校園必將重新走向更全面、更高層次的開放,真正做到大學與社會的和諧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