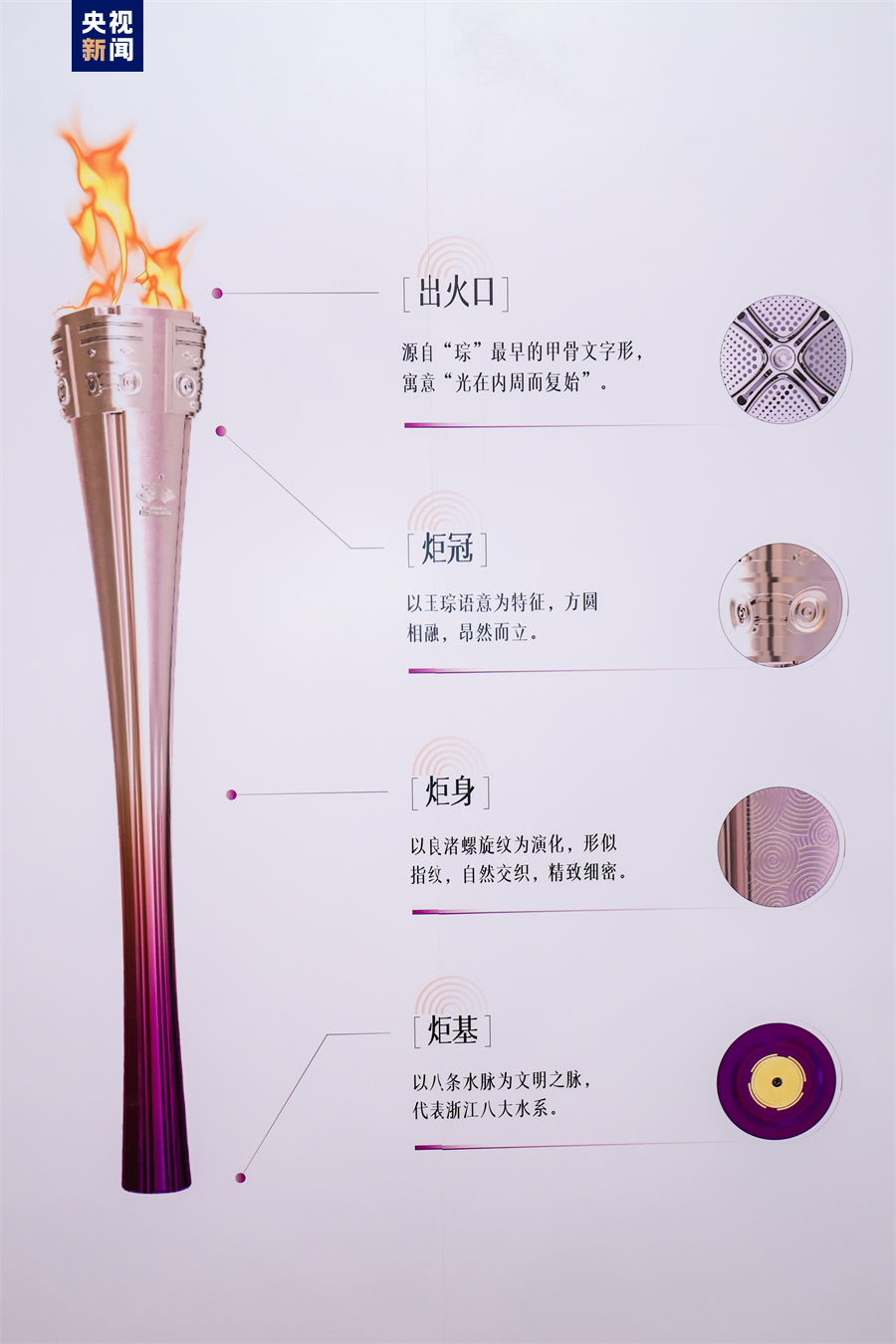馬薩諸塞州白人比例,丹佛白人比例
田野 趙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一種選舉地理的視角
作者:田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當代美國評論》2020年第3期,文中圖表和注釋略;當代美國評論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
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標志著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而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此輪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作為稀缺要素,美國的非熟練型與半熟練型勞動力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進而反對全球化;而作為充裕要素,美國的人力資本從全球化獲益,進而支持全球化。這兩類勞動力要素的地理集聚特征導致了美國選民對于全球化的政策偏好在不同區(qū)域間的分化,包括專業(yè)化經濟區(qū)之間、城市中心區(qū)與外圍區(qū)之間和不同規(guī)模的都市區(qū)之間三種形式的分化。特朗普正是憑借鮮明的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在那些非熟練型和半熟練型勞動力集聚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帶、城市外圍的農村、小規(guī)模城市贏得了更多的選票和支持。
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政治思潮,民粹主義幾起幾落。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起,以反全球化為核心訴求的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開始席卷大西洋兩岸。歐洲民粹主義浪潮不僅表現為英國脫歐,還包括各國民粹主義政黨在政治選舉中的強勢崛起。美國則歷來擁有民粹主義的傳統(tǒng),左翼民粹主義現象包括19世紀90年代的人民黨、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等;而右翼民粹主義則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的排外運動、20世紀30年代教父考福林的反猶運動及20世紀60年代喬治·華萊士的反民權運動,再到1992年羅斯·佩羅及1996年帕特·布坎南的反自由貿易運動和2010年以來的“茶黨”運動。2016年美國大選迎來了美國民粹主義的新一輪抬頭,以桑德斯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同時崛起,共同沖擊著美國的主流價值與政治體系。桑德斯在初選的落敗和特朗普的勝選則彰顯出右翼民粹主義比左翼民粹主義在美國政治中具有更為強勁的勢頭。
作為民粹主義思潮最為直觀的反映,特朗普的競選策略在于通過塑造一種“純潔的人民VS腐敗的精英”的二元對立來迎合民怨并爭取支持。他在競選演講中多次使用“我們”“你們/你”“他們”等語匯,意在將自己構建為“美國人民”的代表,而將主流建制派精英塑造為損害美國利益的“他者”。在指責奧巴馬和希拉里導致美國國內經濟不振和國際安全環(huán)境惡化的同時,特朗大力宣揚自己將奉行“美國優(yōu)先”(America First)原則、“讓美國再次偉大”。執(zhí)政后,特朗普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帶有強烈的以“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標志的右翼民粹主義色彩。與前任建制派推崇的新自由主義路線相反,特朗普將美國如今面臨的眾多困境都歸咎于外國、國際機制、移民等非本土因素,進而實施了眾多逆全球化的政策。具體體現為:一是反對自由貿易,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對主要貿易伙伴施加高額關稅、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等;二是反對移民,比如,在美墨邊境筑墻,頒布法令禁止入境美國,全面驅逐“無證移民”等;三是減少國際義務,包括淡化美國與盟友的聯(lián)系,退出《巴黎氣候協(xié)定》、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一系列國際協(xié)議和機制,終止與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關系等。
無論是在競選過程中還是在當選后的施政過程中,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者都以反全球化作為核心訴求,以此爭取國內那些在全球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失利者。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成為這一輪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鑒于選舉政治地理在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的顯要性,本文將采取一種選舉地理的視角來考察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選民基礎,即通過考察美國國內在全球化中受損群體的地理分布,來推導和驗證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支持率的區(qū)域分化特征。在回顧既有文獻和確立分析框架的基礎上,本文首先結合美國的經濟地理變遷說明其國內要素所有者的區(qū)域分化特征,然后根據美國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說明不同要素所有者的政策偏好分化,進而推導美國國內哪些區(qū)域的選民更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由此提出一系列假說,最后利用2016年美國大選相關數據驗證這些假說。
既有文獻回顧與分析框架
(一)既有文獻回顧
特朗普當選總統(tǒng)后,許多文獻試圖解釋這一“黑天鵝”事件何以發(fā)生。既有文獻主要從經濟利益、身份政治、個體心理三種視角切入,來回答特朗普的選民基礎是什么及其為什么支持特朗普這兩個問題。
首先是經濟利益的視角。關于特朗普當選最普遍的一種解釋是從經濟利益出發(fā),強調“鐵銹帶”經濟就業(yè)狀況持續(xù)惡化的白人工人階級為特朗普提供了贏取勝利的關鍵性選票。刁大明指出,在2016年大選中,共和黨增長最多和減少最多的同步變化群體具有的特征包括“中學教育及以下者”“家庭年收入三萬美元以下者”和“非婚男性”,這一群體基本上就是“銹蝕帶”地區(qū)(指傳統(tǒng)制造業(yè)廣泛分布的美國大湖區(qū)與中西部各州)的藍領中下層選民,因此藍領中下層選民的轉向對特朗普的最終勝利意義重大。張文宗指出,在美國24個“紅州”和16個“藍州”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是“鐵銹帶”的集體轉向促成特朗普以306張對232張選舉人票的優(yōu)勢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tǒng)。莫盛凱尤其關注位于“鐵銹帶”的3個由“藍”轉“紅”的州——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認為特朗普的勝利正是在美國特殊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憑借在這3個州的微弱優(yōu)勢造就的。張毅認為,由于各種因素,“任何共和黨人在2016年大選中都擁有相當高的勝算”。因此,“解釋特朗普為何當選總統(tǒng)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解釋為何特朗普能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而特朗普在初選中的勝利離不開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重要支持。斯蒂芬·摩根(Stephen L. Morgan)等人的數據分析也支持了白人工人階級對特朗普選舉勝利至關重要的說法,尤其是在被特朗普翻轉的6個“關鍵搖擺州”。盡管特朗普還支持許多傳統(tǒng)的共和黨立場,例如去監(jiān)管、減稅、增加國防開支等,但是這僅僅幫他保住共和黨原有的選民基礎,而白人工人階級的額外支持才是勝利的關鍵。
這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之所以轉向支持特朗普,正是由于特朗普反全球化及“把工作帶回美國”的經濟主張迎合了他們的利益訴求。王希指出,隨著全球化加深和美國“去工業(yè)化”加快,中西部和南部地區(qū)的白人工人群體不僅未能享受到全球化紅利,反而遭受了收入和就業(yè)的重創(chuàng),“特朗普將自己說成是‘被遺忘的’中下層白人的代言人,將中下層白人的痛苦歸咎于‘建制派’政治精英對美國人的欺騙,將全球化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出賣和犧牲”,從而導致這些地區(qū)的白人藍領工人從支持希拉里轉向特朗普。強舸在分析曾經的核心支持者——“銹帶”藍領改換門庭的原因時,更加強調對于白人藍領所遭受的全球化沖擊缺乏有效回應。周琪等持有類似觀點,認為作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是中下層白人,或者說是白人藍領階層,在兩黨選民中都屬于被忽視的群體,因此特朗普的出現為他們表達憤怒和改變現狀提供了一種選擇。莎倫·蒙納特(Shannon M. Monnat)發(fā)現特朗普在、酗酒現象普遍和自殺死亡率較高的縣獲得了較多的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工業(yè)區(qū)和新英格蘭地區(qū)的城鎮(zhèn)和農村,這些地區(qū)往往工人階級眾多,且在過去幾十年經歷了制造業(yè)的嚴重衰退,而特朗普“振興制造業(yè)”的競選承諾恰恰迎合了這些身處經濟困難與絕望中的選民的訴求。
其次是身份政治的視角。盡管基于經濟利益視角的階級解釋十分流行,但也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單純的經濟因素無法提供充分解釋,他們強調種族、性別及宗教信仰等身份政治議題在特朗普吸引選民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甚至更大的作用。祁玲玲指出,2016年大選實際上超越了傳統(tǒng)的就業(yè)、經濟議題,其后蘊藏的核心沖突并不是不同教育程度或不同經濟利益、社會階層的群體之間的對抗,而主要是一場關于“政治正確”與“反政治正確”的觀念對抗,或者說是價值觀沖突,而這種沖突集中體現在意識形態(tài)、種族問題、多元文化幾個方面。大衛(wèi)·諾曼·史密斯(David Norman Smith)等人也認為,選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原因并非源自經濟壓力,而是由于他們認同特朗普的觀念結構,其中就包括了對移民、婦女、的偏見。諸多數據分析支持了這種觀點。泰勒·雷尼(Tyler T. Reny)發(fā)現,持有種族保守態(tài)度和持反移民態(tài)度的白人選民更傾向于支持特朗普。納齊塔·拉杰瓦迪(Nazita Lajevardi)發(fā)現,選民對于美國的怨恨是預測其支持特朗普行為的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凱特·拉特里夫(Kate A. Ratliff)等人發(fā)現,較高程度的性別歧視預示著支持特朗普的更大可能性。喬安德魯·懷特海德(Andrew L. Whitehead)等人發(fā)現,美國民族主義在預測特朗普得票率方面也發(fā)揮了重要且獨立的影響。凱倫·布萊爾(Karen L. Blair)也發(fā)現,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有可能是種族主義者和仇視、變性人及同性戀的選民。
在對上述觀點和現象進行解釋時,布倫達·梅杰(Brenda Major)認為,由于美國非白人人口不斷增長,甚至有望在21世紀中葉超過白人,白人群體的身份地位與影響力正在面臨威脅。因此,美國白人對于自己種族群體的認同度越高,對于種族多樣性的接納度就越低,進而就越容易支持特朗普及其反移民主張。而在解釋為什么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和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這兩個群體在支持特朗普的傾向上存在巨大分化時,布萊恩·夏弗納(Brian F. Schaffner)等人認為,雖然經濟困境可以部分地解釋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在于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群體更容易對不同種族或女性懷有敵意,因此更傾向于支持持有相似立場的特朗普。納森·羅斯威爾(Jonathan T. Rothwell)等人在分析為什么特朗普的支持者往往生活在遠離墨西哥邊境的白人聚集區(qū)和大學畢業(yè)生比例較低的地區(qū)時,認為這些地區(qū)與其他種族、移民及大學畢業(yè)生的接觸相對有限,因此助長了種族偏見與文化誤解的形成。露絲·布朗斯坦(Ruth Braunstein)則強調特朗普宣傳策略所發(fā)揮的作用。特朗普在大選中將宗教少數派構建成局外人(outsiders)、敵人(enemies)和其他人(others),從而有效地吸引了排斥或恐懼難民的選民群體。
最后是個體心理的視角。少數學者對特朗普當選的分析聚焦于心理學視角,該視角主要關注主觀層面而非客觀層面,將特朗普對于選民的吸引歸結于選民所經歷的某種消極的心理狀態(tài)或情緒情感,而非由經濟或社會等因素引發(fā)的真實不幸。曾向紅和李琳琳提出,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在20世紀80年代后的社會變遷中,經歷著愈來愈嚴重的身份焦慮,而特朗普的出現為深受身份焦慮困擾的白人提供了情緒宣泄的機會。戴安娜·穆特扎(Diana C. Mutz)反對將2016年大選的結果解釋為地位較低的經濟失利者對于主流政黨的反擊,認為特朗普當選的主要因素來自地位較高的主流群體對于自身地位的焦慮,日益發(fā)展的國內種族多樣性和全球化引發(fā)了關于美國白人種族地位和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不安全感,這種關于地位的威脅感(status threat)是特朗普獲取支持的主要來源。克里斯汀·韋利(Christine J. Walley)也認為,特朗普的選民不能只局限于“未獲得學士學位”的“工人階級”,強調還包括某些比較富裕的保守派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后者支持特朗普的原因一方面基于特朗普的白人身份政治,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美國日益擴大的經濟不平等所引發(fā)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不是源于現有的經濟困難,而是源于對未來階級地位下滑的擔憂。理查德·福特(Richard C. Fording)等人認為,“低信息選民”(low information voters)更傾向于投票給特朗普,這類選民缺乏對基本事實的把握,認知和推理能力相對匱乏,因此他們的投票行為主要受到情緒或情感的驅動,特朗普正是通過激發(fā)和利用這類選民的恐懼、焦慮、憤怒及仇恨的心理來爭取選票。托馬斯·佩蒂格魯(Thomas F. Pettigrew)也強調心理作用而非實際處境,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總是真的在經濟狀況或身份地位方面處于困境,但是他們自身所感到的被剝奪感及威脅感總是較高。
上述文獻對于特朗普的選民基礎及其勝選原因提供了較為多樣的解釋視角。不可否認,特朗普的勝選雖然在事實上是由經濟利益、身份政治、個體心理等各種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但筆者認為,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經濟因素發(fā)揮了最為根本和重要的作用。正如皮尤研究中心于2016年9月開展的一項調查所顯示的,經濟仍然是選民最為關心的問題。就經濟角度的解釋而言,盡管已經有許多研究揭示了特朗普反全球化的主張和美國藍領中下層選民之間的關鍵聯(lián)系,但多數文獻只停留在描述性分析的層面,鮮少能從理論上就美國中下層白人為何反對全球化這一重要問題予以說明。此外,在美國的選舉制度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依據選區(qū)劃分在大選中投票,選民的地理分布可以為解讀其政治行為提供重要的依據。但是既有的文獻大多關注選民的個體特征,如性別、年齡、種族、學歷、信仰和收入等因素如何影響投票行為,而很少從選舉地理的路徑分析特朗普勝選的選民基礎。本文旨在彌補上述不足,從選舉地理的視角分析全球化如何塑造特朗普的選民基礎。
(二)分析框架:全球化、要素稟賦與政策偏好的區(qū)域分化
關于全球化如何塑造國內不同社會行為體的政策偏好,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已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作為這一研究議程的倡導者,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海倫·米爾納(Helen Milner)提出,“由于政治和經濟如此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有理由期待會發(fā)生深遠的政治影響——尤其是世界各國的國內政治應該體現出世界經濟的影響”。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文獻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 Ohlin)模型和斯托爾珀-薩繆爾森(Stolper Samuelson)定理為基礎,解釋了國家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如何影響國內的政治分化。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一個國家所出口的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對充裕的生產要素,而進口商品往往需要密集使用其相對稀缺的要素。而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則揭示了該模型在一國內部所帶來貿易收入的分配效應,即貿易將會提高該國充裕要素所有者的實際報酬,降低該國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報酬。因此,一個國家內部的充裕要素所有者往往將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往往反對全球化和尋求貿易保護。在當代世界,發(fā)達國家往往人力資本要素相對充裕、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相對稀缺。基于自身的相對充裕或稀缺程度,發(fā)達國家的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一般具有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政策偏好,而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一般具有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的政策偏好。
根據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往往會在不同類型的地區(qū)內形成集聚,由于不同類型的生產活動所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存在差異,所以集聚將導致生產要素的區(qū)域分化。一般而言,發(fā)達國家的集聚主要存在三種形式,分別是專業(yè)化經濟區(qū)之間的分化、城市中心區(qū)與城市外圍區(qū)的分化和不同規(guī)模城市之間的分化。較高水平的產業(yè)集聚一般導致專業(yè)經濟區(qū)的形成,如傳統(tǒng)工業(yè)區(qū)、高科技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聚集區(qū)。此外,傳統(tǒng)制造業(yè)也更多地分布于城市外圍的郊區(qū)、農村或人口規(guī)模較小且土地租金較低的小城鎮(zhèn),而高新技術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則更多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區(qū)或人口規(guī)模較大、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大都市。因為傳統(tǒng)制造業(yè)主要密集使用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而高新技術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主要密集使用擁有較高知識技能的人力資本,所以這兩種勞動力要素在區(qū)域分布上形成差異,即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主要分布在傳統(tǒng)制造業(yè)帶、城市外圍區(qū)、小城鎮(zhèn),而人力資本主要分布在高科技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聚集區(qū)、城市中心區(qū)、大都市。考慮到勞動力構成各區(qū)域選民的大多數,可以基于不同性質的勞動力要素在不同區(qū)域中的地理分布得到不同區(qū)域選民政策偏好的分化模式。
美國經濟地理變遷與要素所有者的區(qū)域分化
經濟地理特征描述了各種產業(yè)類型在不同區(qū)域的分布概況。伴隨著產業(yè)結構的變化,美國的經濟地理特征自19世紀末以來經歷了重大變遷。不同要素所有者隨著不同類型產業(yè)在各區(qū)域間的集聚而集聚,最終形成了專業(yè)化經濟區(qū)之間、城市中心區(qū)與城市外圍區(qū)之間和不同規(guī)模城市之間三種區(qū)域分化形式。
(一)專業(yè)化經濟區(qū)之間的分化
美國在立國之初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yè)國。隨著兩次工業(yè)革命的發(fā)生,美國工業(yè)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在1884年首次超過農業(yè),但美國工業(yè)的早期發(fā)展在地區(qū)布局方面并不均衡。美國制造業(yè)的發(fā)源地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期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qū),當時這些地區(qū)的造船業(yè)、木制品和肉類加工業(yè)等已經初具規(guī)模。19世紀中后期,美國北部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出現局部擴散,部分制造業(yè)從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地區(qū)逐步向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qū)轉移,到20世紀初基本形成了以新英格蘭、中大西洋和中西部為代表的北方制造業(yè)帶。而在美國全國范圍內,在南北戰(zhàn)爭爆發(fā)前,北部的工業(yè)革命基本完成,并集中了全國90%以上的工業(yè),如紡織業(yè)、鋼鐵業(yè)、機械制造業(yè);而此時南部和西部仍以農業(yè)經濟為主,工業(yè)基礎十分薄弱。到19世紀下半葉,當美國北部開始進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時,工業(yè)革命才逐步開始向南部和西部擴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美國工業(yè)總體來說增長強勁,但逐漸呈現出新的區(qū)域分化特征,北部制造業(yè)帶的傳統(tǒng)工業(yè)生產逐步走向停滯或產量下降,而南部和西部則由于新興工業(yè)部門的迅速發(fā)展,躍升為美國新的重要工業(yè)區(qū)。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是美國工業(yè)在整體上迅速發(fā)展的時期,但分布于東北部和五大湖地區(qū)的鋼鐵工業(yè)和機械工業(yè)卻發(fā)展勢頭趨緩,例如,美國的鋼產量在1955年以后一直徘徊在一億噸左右的水平而無較大增長。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集中分布于五大湖區(qū)各州的汽車工業(yè)也出現了停滯。1966年至1971年間,美國每年的汽車產量都低于1965年的1105.7萬輛的水平,尤其在1967年和1970年產量兩次下降至900萬輛以下。與之相對,美國化學工業(yè)的產值在60年代增長了一倍,其生產中心也開始從大西洋沿岸中部向南轉移,南部的得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墨西哥灣沿岸日益成為新的化學工業(yè)區(qū)。此外,西部太平洋沿岸地區(qū)的電子工業(yè)也迅速崛起。1950至1970年,美國電子工業(yè)產值增加了八倍多,電子計算機的生產規(guī)模、技術水平和應用程序都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在結束了長達十年的經濟“滯脹”后,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加速發(fā)展高科技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這進一步深化了不同區(qū)域之間的產業(yè)分化格局,最終形成了以五大湖地區(qū)“鐵銹地帶”和東西海岸高新技術和高端服務聚集區(qū)為代表的不同經濟區(qū)。一方面,傳統(tǒng)制造業(yè)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分布于五大湖地區(qū)的紡織、鋼鐵、玻璃、汽車工業(yè)等紛紛淪為“夕陽產業(yè)”,在技術進步和國際競爭等因素的推動下走向了長期衰退,陷入工廠倒閉、機器生銹的境地。盡管奧巴馬政府曾推出“再工業(yè)化”的措施,但仍很難改變該地區(qū)的總體頹勢。另一方面,高科技產業(yè)和高端服務業(yè)成為美國的新興經濟基礎。美國西海岸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硅谷作為世界著名的高科技產業(yè)區(qū),最早以研究與生產半導體芯片及先進的計算機與電子工業(yè)聞名,這里集聚了蘋果、惠普、英特爾、谷歌和臉書等眾多科技創(chuàng)新企業(yè)的總部,如今該地區(qū)在微電子技術、通信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等眾多科技領域都形成了產業(yè)集聚。此外,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和大西洋中部地區(qū)也進行了深刻的產業(yè)結構變革,生產務業(yè)迅速發(fā)展并取代傳統(tǒng)制造業(yè)成為該地區(qū)的主導產業(yè),金融保險、管理咨詢、教育和醫(yī)療等高端服務業(yè)在此聚集。
(二)城市中心區(qū)與城市外圍區(qū)之間的分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工業(yè)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兩類工業(yè)生產活動幾乎主導了當時的城市經濟。一類是大規(guī)模原料密集型制造業(yè)=活動,基于交通便利性的考量,這類活動往往靠近鐵路和水運設施分布,典型=代表是匹茲堡的鋼鐵生產、芝加哥的屠宰和肉類包裝、新奧爾良的制糖和明尼阿波利斯的面粉加工;另一類是小規(guī)模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活動,如服裝、印刷、皮革、珠寶、鐘表、家具和專業(yè)金屬加工。
然而,在美國現代工業(yè)發(fā)展之初,甚至早在19世紀中葉,工業(yè)布局就顯現出從城市中心向郊區(qū)和農村等外圍地區(qū)緩慢分散的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這一擴散進程開始顯著加快。隨著工廠從城市中心地區(qū)向城市外圍遷移,中心地區(qū)制造業(yè)就業(yè)逐步下降,郊區(qū)和農村地區(qū)制造業(yè)就業(yè)隨之增加。例如,1958至1967年,中心城區(qū)制造業(yè)就業(yè)年增長率只有0.7%,而郊區(qū)則高達3.1%。1947至1972年,人口規(guī)模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qū)(Metroplitan Areas)內,中心城市的制造業(yè)工作崗位減少了88萬個,而這些城市郊區(qū)帶的制造業(yè)工作崗位卻增加了250萬個。1967至1972年,農村地區(qū)和非都市區(qū)(Non Metroplitan Areas)也以11.3%的增長率成為重要工業(yè)的遷移地。20世紀80年代,當進口競爭迫使國內制造商降低成本時,制造業(yè)進一步向工資、財產稅和土地價格普遍較低的農村地區(qū)轉移,并且這種趨勢一直延續(xù)到21世紀初。
伴隨著制造業(yè)從城市向郊區(qū),再向農村的不斷遷移,農村及遠郊日益成為美國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大本營。與通常和農村相關的農業(yè)與礦業(yè)等部門相比,制造業(yè)在農村地區(qū)提供了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和更高的收入。到2000年,只有5%的非都市區(qū)勞動力受雇于農業(yè)。2015年,美國農村的制造業(yè)崗位總數為250萬個,而農業(yè)崗位為140萬個、采礦崗位(包括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為50萬個。2015年,農村收入包括1.581億美元的制造業(yè)收入、4540萬美元的農業(yè)收入和3730萬美元的采礦業(yè)收入。隨著美國經濟去工業(yè)化的總體趨勢,2001年至2015年期間,農村制造業(yè)就業(yè)也有所下降,但相對而言,制造業(yè)對農村經濟的重要性仍然大于對城市經濟的重要性。盡管美國制造業(yè)就業(yè)的總體份額不斷下降,但2015年制造業(yè)就業(yè)仍占農村私人非農就業(yè)的14%,城市僅為7%;而2015年制造業(yè)收入占農村私人非農業(yè)收入的21%,城市僅為11%。就制造業(yè)類型而言,轉移到農村地區(qū)的制造業(yè)主要是木材制品、食品、塑料、橡膠、家具、紡織品、機械制造等傳統(tǒng)工業(yè)部門,大部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部門仍然保留在城市。例如,2015年,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制造所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占城市總制造業(yè)就業(yè)的10%以上,但只占農村制造業(yè)就業(yè)的約2%。
中心城市在制造業(yè)外遷的過程中,完成了從生產中心向信息與服務中心的轉變,成為金融、保險、法律、行政和商業(yè)服務活動的集聚區(qū)。城市地區(qū)辦公室面積的持續(xù)增加凸顯了城市在國民經濟中所具備的管理與決策職能。1960至1970年間,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中心商業(yè)區(qū)的辦公面積平均增長了約38.8%。隨著美國去工業(yè)化進程的發(fā)展,美國大部分制造業(yè)已經轉移到大都市區(qū)外圍乃至海外,但是在美國大都市區(qū)內尤其是中心區(qū)內,仍然保留了一定數量的制造業(yè)企業(yè),這些制造業(yè)往往與高級服務業(yè)或時尚消費品生產密切相關,如印刷制品、通信設備、珠寶首飾等,這些產業(yè)要么需要與城市商業(yè)客戶保持經常的聯(lián)系與接觸,要么需要緊跟飛速的技術進步或多變的市場潮流。美國中心城區(qū)作為高端服務業(yè)、信息產業(yè)和文化產業(yè)的大本營,吸引了眾多高科技公司、藝術工作者和其他創(chuàng)新人才聚集于此。例如,紐約市中心區(qū)曼哈頓不僅擁有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集中了美林證券、高盛、摩根士丹利、紐約證券交易所等著名金融機構和上百家大公司的總部,而且也是美國現代歌舞劇中心百老匯和大都會博物館、古根海姆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等世界著名藝術場館的所在地。除了曼哈頓以外,波士頓市的中心區(qū)也是東海岸重要的商業(yè)中心,這里除了是美國銀行、普華永道和富達投資等大型金融與商業(yè)公司的所在地,還是美國高等教育中心和生命科學與生物制藥產業(yè)集群地。
(三)不同規(guī)模城市之間的分化
美國城市的發(fā)展主要體現為大都市區(qū)的形成和發(fā)展。美國的大都市區(qū)在20世紀初形成,其生態(tài)組織結構一般包括一個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中心城市(人口至少5萬人)以及與該中心地區(qū)有著較高的經濟與社會整合程度的周邊郊區(qū)。盡管大都市區(qū)的經濟相對于非都市區(qū)的農村經濟而言,更多地依賴生產務業(yè)與高科技產業(yè),但是在大都市區(qū)內部層級中,不同規(guī)模的大都市區(qū)在產業(yè)結構和勞動力類型方面仍然存在差異。
相對而言,大型城市主要以創(chuàng)新型和定制型的經濟活動為主,如微電子、軟件、生物技術、商業(yè)服務、金融、藝術、時尚等;而在小型城市更普遍的仍是標準化和常規(guī)化的制造業(yè)工作,如建筑、維修、運輸等。科技含量較高的制造業(yè)也更傾向于集聚在規(guī)模較大的大都市區(qū)內。2010年,美國95%的尖端高科技制造業(yè)就業(yè)位于大都市區(qū),其中79.5%集中在100個最大的大都市區(qū)內。尖端高科技制造業(yè)主要包括計算機和電子產品制造、醫(yī)藥制造、航空航天產品和零部件制造。其中,計算機與電子產業(y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莫過于西海岸硅谷所在的圣何塞-桑尼維爾-圣克拉拉都市區(qū)(San Jose-Sunnyvale Santa Clara, CA),生物醫(yī)藥產業(yè)則集中分布于東北部的波士頓-劍橋-牛頓都市區(qū)(Boston Cambridge Newton, MA-NH),而航空航天產業(yè)集聚區(qū)主要位于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塔科馬-貝爾維尤都市區(qū)(Seattle Tacoma Bellevue, WA)。這類產業(yè)之所以選擇集聚于大都市區(qū)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區(qū),是由于在這些區(qū)位能夠更容易地接觸到科學家和工程師、供應商、客戶,便于與同行公司進行便捷的信息分享,以及享受高質量的商業(yè)支持和工程服務等,而這些區(qū)位優(yōu)勢對于以研發(fā)新產品與新技術為導向的高科技制造業(yè)企業(yè)而言尤其重要。
與產業(yè)結構在不同規(guī)模城市間的分化相對應,美國不同層級城市所具備的勞動力類型也存在高低分化。研究表明,與認知能力(數學推理、思維邏輯、說服力等)相關的人力資本指數顯示出與城市規(guī)模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與體力相關的勞動力指數與城市規(guī)模有著強烈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高級認知工作往往集中在頂端的大城市,而普通體力工作往往集中在底端的小城市。所謂高級認知工作,往往對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有較高的要求,所需要的勞動力類型即人力資本/人才,一般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技術人員、管理人才、政府公務人員等;而從事普通體力工作的即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主要依賴于勞動者的力量耐力、手工技巧和機械技能,包括手藝工匠、工廠工人等。與產業(yè)集聚類似,人力資本分布也具備地理集聚特征,人才集聚與高技術產業(yè)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人才對于高技術產業(yè)的創(chuàng)新與競爭而言至關重要,二者所集聚的地區(qū)往往也是經濟收入較高的地區(qū)。例如,美國第十大城市、加利福尼亞州第三大城市圣何塞位于硅谷的核心地帶,市內及周邊分布著眾多的高等學府和科技公司,因而也成為工程學、計算機科學和商學畢業(yè)生的聚集地。據調查,2016年,圣何塞所在的大都市區(qū)吸引了67億美元的針對科技初創(chuàng)企業(yè)的風險投資,投資規(guī)模在所有大都市區(qū)中排名第三。與之相對應的是,該都市區(qū)知識型人才(workers in knowledge occupations)的比例和技術型人才(techworkers)的比例分別為36%和27.5%,均名列全美第一。
美國參與全球化的要素稟賦與政策偏好區(qū)域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霸權,在眾多科學技術領域獨占鰲頭,這與其較高的教育水平及人才優(yōu)勢密切相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fā)布的《2017年全球人力資本報告》,美國的全球人力資本指數為74.84,在測算的130個國家中排名第四。由此可見,美國是人力資本要素相對充裕的國家。由于要素劃分的相對性,一個勞動力無法同時被定義為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和非熟練與半熟練勞動力。與美國充裕的人力資本要素相比,作為生產要素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則處于相對稀缺的狀態(tài)。由于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一般未接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因此可以用低學歷勞動力在總勞動力人口中的占比來衡量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程度。根據國勞工部勞工統(tǒng)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發(fā)布的數據,2016年,美國勞動力人口(25歲及以上)中擁有高中文憑以及高中未畢業(yè)的人口占比僅為33.6%,余下大約66.4%的勞動力人口都至少接受過某種大學教育(包括接受過大學教育但未獲得學位和獲得副學士、學士及以上學位的幾種情況)。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中是處于相對少數的。這樣,美國兩種勞動力要素的相對稟賦為人力資本相對充裕、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相對稀缺。
基于這種要素稟賦,根據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美國所出口的商品或服務應當包含密集程度較高的人力資本要素,而進口商品或服務則包含密集程度較高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公布的2016年美國商品和服務進出口統(tǒng)計數據,美國在參與國際貿易時主要以進口商品和出口服務為特征,由于服務行業(yè)相較于生產行業(yè)一般需要更多的人力資本或更少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因此僅從美國總的貿易結構來看即符合理論推測。具體而言,美國雖然在大多數商品貿易領域都存在較大的逆差,尤其是在汽車及其零部件和發(fā)動機、服裝和鞋類、廚具及其他家庭用品三類傳統(tǒng)制造業(yè)領域。但是在民用飛機及其發(fā)動機和零部件、化學材料、科學儀器和醫(yī)院醫(yī)療器械等領域仍以出口為主;在服務貿易領域,美國僅在運輸服務、保險服務和計算機服務等少數領域存在逆差,而在其余服務類別中均以出口為主,尤其是在知識產權服務、金融服務、個人旅行服務(包括健康、教育及其他)、專業(yè)和管理咨詢服務等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領域存在較大順差。由此,美國在不同商品和服務類別中的進出口情況基本符合其要素稟賦特征。在此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根據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推導出美國不同勞動力要素所有者在全球化中的受益與受損效應,即人力資本要素所有者受益,而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受損。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產業(yè)興衰的變化驗證了全球化在國內不同要素所有者間產生的利益分配效應。一方面,美國制造業(yè)特別是傳統(tǒng)制造業(yè)在全球化進程中走向衰退,大批工廠工人陷入收入困境與失業(yè)危機。隨著全球化深化以及技術進步,美國大量依賴低技能勞動力的制造業(yè)崗位轉移至海外成本更低的地區(qū),國內工廠也由于難以與價格低廉的進口產品進行競爭而瀕臨倒閉,從而加大了美國國內就業(yè)的壓力。從生產總值來看,美國制造業(y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1953年達到28%的峰值以來普遍下降,并從2001年的14%下降到2015年的12%。從就業(yè)崗位來看,美國制造業(yè)的工作崗位數從1979年的1940萬個的峰值下降至2010年的1150萬個,降幅高達40.7%,且2010年制造業(yè)的崗位數僅占所有崗位數的8.5%。美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于1973至2017年僅增長12.4%,也遠遠落后于同期生產率77%的增長。
另一方面,美國在高端服務業(yè)和先進制造業(yè)領域占據全球優(yōu)勢,金融界人士、企業(yè)高管、科學家、工程師等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變得愈發(fā)富有。盡管美國傳統(tǒng)制造業(yè)陷入長期衰退,但是由高科技所驅動的高端服務業(yè)和先進制造業(yè)在美國經濟與就業(yè)中的地位始終保持強勢。1996至2016年,美國高科技產業(yè)的經濟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始終維持在18%左右,在總就業(yè)中的份額也始終保持在9.2%至10.1%區(qū)間。即使是在金融危機后美國經濟總體衰退的時期,高科技產業(yè)的表現也依然保持穩(wěn)定甚至有所增長。從2007年到2010年,美國高科技產業(yè)的產出份額從17.8%增至18.7%,并在此后的六年間一直保持在18.1%以上,就業(yè)份額也從2007年的9.3%增至2010年的9.8%。在此期間,盡管高科技產業(yè)的就業(yè)崗位數有略微下降,但是很快在2011年得以恢復,而非高科技行業(yè)直到2014年才超過衰退前的就業(yè)水平。不僅如此,高科技產業(yè)從業(yè)者的工資水平也普遍高于非高科技產業(yè)的工資水平。例如,2016年,高科技產業(yè)中從事管理職位者年工資的中位數為131410美元,而非高科技產業(yè)中從事該職位者年工資的中位數僅為92220美元。
由于美國產業(yè)分布具備地理集聚特征,而不同產業(yè)對應不同類型的勞動力要素,所以全球化對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影響,可進而表現為不同區(qū)域選民之間在政策偏好上的分化。
首先,就專業(yè)經濟區(qū)的分化而言,中西部五大湖區(qū)域的制造業(yè)帶經歷了嚴重的就業(yè)萎縮與人口外流,從美國曾經最重要的工業(yè)區(qū)淪為如今的“鐵銹帶”。從地理劃分來看,中西部地區(qū)主要包括伊利諾伊、印第安納、艾奧瓦、密歇根、密蘇里、明尼蘇達、俄亥俄、威斯康星、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亞十個州。2000至2018年,這十個州提供的就業(yè)比重從23.42%降至20.72%,與此同時,該地區(qū)的人口占全美總人口的比重也從2000年的22.87%下降至20.82%。其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諾伊州的經濟衰退最為嚴重,這三個州在此十年間的就業(yè)比重分別下降了0.57個百分點、0.55個百分點和0.49個百分點,人口比重分別下降了0.45個百分點、0.47個百分點和0.51個百分點。然而,分別位于東西海岸的華爾街和硅谷則成為美國經濟領跑全球的新引擎,依靠發(fā)達的金融產業(yè)和先進的科技革新,不僅吸引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也創(chuàng)造了美國接近一半的財富。金融業(yè)發(fā)達的東北部地區(qū)主要包括康涅狄格州、特拉華州、緬因州、馬里蘭州、馬薩諸塞州、新罕布什爾州、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羅得島州和佛蒙特州。以華爾街所在的紐約州為例,2000至2018年,該州吸納的就業(yè)人數比重從6.3%增至6.32%;而太平洋沿岸地區(qū),包括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和加利福尼亞州,2000至2018年這三州的就業(yè)比重分別增加了0.14個百分點、0.02個百分點和0.44個百分點。此外,美國東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區(qū)雖然所涵蓋的地理范圍僅限14個州,但卻在2018年為美國的GDP貢獻了高達40.52%的份額。
其次,城市中心區(qū)與城市外圍區(qū)尤其是農村地區(qū)之間在貧困率、失業(yè)率、工資水平方面也存在明顯差距。自20世紀60年代貧困率被官方統(tǒng)計以來,非都市區(qū)和農村地區(qū)的貧困率一直高于大都市區(qū)。2017年,大都市區(qū)貧困率為12.9%,而農村貧困率達到16.4%。而且,在2016年,35%的城市居民和31%的郊區(qū)居民擁有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農村地區(qū)只有19%的高學歷人口,而高人力資本水平往往與高工資相對應。所以從人均收入來看,也是城市地區(qū)最高、農村地區(qū)最低。一項由5006名成年人參與的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生活在美國農村的白人中有69%的人聲稱難以在所居住的社區(qū)內找到工作,而生活在郊區(qū)和城市的白人中認同該項的比例分別為54%和45%。有65%的人認為,日益增多的移民正在搶走工作機會(郊區(qū)和城市的比例分別為52%和48%);33%的人對后代的財務狀況持悲觀態(tài)度(郊區(qū)和城市的比例分別為28%和23%)。這主要是由于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農村選民比城市和郊區(qū)選民更易遭遇經濟困境。
最后,較大規(guī)模的大都市區(qū)在美國經濟與就業(yè)中占據著更顯著的地位,也相應擁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發(fā)布的數據,2016年,美國規(guī)模最大的前十個都市區(qū)實際的GDP平均為5693.5億美元,其中美國第一大都市區(qū)紐約-紐瓦克-澤西城(New York Newark Jersey City,NY-NJ-PA)以約14800.3億美元大幅領先;而規(guī)模最小的十個都市區(qū)在2016年實際的GDP平均只有38.6億美元,僅為前十大都市區(qū)平均水平0.6%。在提供就業(yè)方面,2016年,前十大都市區(qū)平均提供的就業(yè)崗位為5492287個,而排在末尾的十個都市區(qū)在該年平均只提供了45857個就業(yè)崗位。此外,那些收入水平較高的大都市區(qū)往往也屬于人口規(guī)模較大的類型。據統(tǒng)計,2016年,在美國的382個都市統(tǒng)計區(qū)中,家庭收入中位數最高的前十個都市區(qū)中有八個在人口規(guī)模排名中位列前100名,并且有五個都市區(qū)位列前50名。家庭收入中位數最低的十個都市區(qū)在都市規(guī)模排名中也普遍落后,其中有九個排在第100名之后、七個排在第200名之后。
因此,由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所集聚的地區(qū)(制造業(yè)帶、城市外圍區(qū)、小型城市)在全球化中受到嚴重沖擊,往往面臨著較高的失業(yè)率、貧困率或較低的工資水平;而那些由人力資本要素所集聚的地區(qū)(東西海岸、城市中心區(qū)、大型城市)的情況相對較好,是全球化的獲利者。由于特朗普秉持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向選民承諾重新談判貿易協(xié)議和把制造業(yè)就業(yè)帶回美國,所以可以推測特朗普在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聚集的地區(qū)將獲得更多的支持,由此可提出以下三個假說:
假說一,中西部的“鐵銹帶”選民在總統(tǒng)選舉中更傾向支持特朗普。
假說二,位于城市外圍的遠郊及農村地區(qū)選民在總統(tǒng)選舉中更傾向支持特朗普。
假說三,人口規(guī)模較小的大都市區(qū)選民在總統(tǒng)選舉中更傾向支持特朗普。
2016年大選特朗普選民基礎的區(qū)域分化
2016年11月9日,美國大選終于落下帷幕。盡管特朗普以2.1個百分點的劣勢、近287萬張的選票輸掉了普選,但他卻以306比232的選舉人票優(yōu)勢擊敗候選人希拉里,最終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tǒng)。由于特朗普是商人出身且毫無政治經驗,而希拉里則是擁有豐富經驗的資深政客,所以這次大選的結果可謂是超出了世界范圍政界與學界人士的普遍預期。在分析2016年大選結果的眾多文獻中,大部分的觀點都認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往往是未受過高等教育、收入相對較低、年齡相對較大的白人男性。而這些正是美國工薪階層或稱之為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典型特征,他們往往分布在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集聚地,這些地區(qū)是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沖擊最嚴重的地區(qū)。本文將從三種區(qū)域分化形式切入,考察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支持者的區(qū)域分布特征,以檢驗上文所述的三個假說。
首先,從經濟區(qū)的分化來看,特朗普在太平洋沿岸和東北部地區(qū)的得票率均不敵希拉里,但是在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qū)贏得了關鍵優(yōu)勢。如表2所示,特朗普在高科技企業(yè)聚集的太平洋沿岸地區(qū)的平均得票率為35.8%,遠低于希拉里54.7%的成績,尤其是在硅谷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特朗普得票率只達希拉里的一半,而且特朗普未能贏得太平洋地區(qū)任何選舉人票。在金融業(yè)發(fā)達的東北部各州,希拉里的平均得票率同樣高達54.11%,而特朗普僅獲得了39.6%的選票,在該地區(qū)11個州中只拿下了賓夕法尼亞州一州的選舉人票,且只憑借0.7個百分點的微弱優(yōu)勢勝出。特朗普的優(yōu)勢主要體現在西部高山區(qū)及中部大平原、南部地區(qū)、中西部地區(qū)三大區(qū)域。其中,西部高山區(qū)和中部大平原地區(qū)以及南部地區(qū)歷來是傾向共和黨的傳統(tǒng)“紅州”,特朗普得以勝利取決于關鍵的中西部地區(qū)。2016年,特朗普在中西部地區(qū)平均獲得了52.35%的選票,比希拉里的得票率高出10個百分點。而且,特朗普在中西部地區(qū)所贏得的選舉人票數與2012年的共和黨候選人相比增加了一倍多,是共和黨自1988年大選以來在中西部地區(qū)選舉人票方面的最佳表現。
特朗普在中西部地區(qū)的優(yōu)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該地區(qū)的幾個“搖擺州”(swing state)的勝利,包括俄亥俄州、艾奧瓦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這些州同時也位于五大湖沿岸制造業(yè)嚴重衰退的“銹帶”地區(qū)。其中,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分別自1984年大選和1988年大選以來首次從支持轉向共和黨,這些長期“親藍”州在2016年大選中的“翻紅”離不開經濟因素的直接影響。雖然傳統(tǒng)上代表著產業(yè)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奧巴馬政府執(zhí)政的八年期間,美國的國際經濟政策延續(xù)了新自由主義路線,繼續(xù)擁抱自由貿易,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拋棄”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和工人群體。而特朗普的競選主張明確表示要重振制造業(yè)和增加就業(yè),這無疑迎合了“銹帶搖擺州”藍領中下階層選民的利益訴求。因此,就經濟區(qū)分化而言,假說一是符合特朗普的實際得票情況的。
其次,在城市中心區(qū)與外圍區(qū)的分化方面,特朗普的支持率呈現出從城市中心到城市外圍逐漸遞增的特征。在城市地區(qū),特朗普的得票率僅為35%,與希拉里的59%得票率相比存在較大差距。而在郊區(qū),特朗普和希拉里可謂勢均力敵,最終特朗普以50%對45%的微弱優(yōu)勢勝出。與之相對,特朗普在農村地區(qū)卻輕松獲得了62%的選票,希拉里則只獲得34%的選票。
盡管在美國選舉中的城鄉(xiāng)分化歷來存在:農村選民一般更傾向于投票支持共和黨,城市選民則傾向支持,但是2016年大選中的城鄉(xiāng)差異較以往有所擴大,這一點突出地體現為共和黨在農村地區(qū)的得票率獲得較大增加。從2008至2016年,共和黨總統(tǒng)候選人在城市和郊區(qū)的支持率基本沒有變化,但是在農村的選票份額相較于2008年的53%增加了9個百分點。由此可見,特朗普進一步夯實了共和黨在農村地區(qū)的選民基礎。特朗普在城市中心區(qū)與外圍區(qū)之間的得票情況符合假說二。
最后,就不同規(guī)模的城市而言,特朗普的支持率隨著都市區(qū)人口規(guī)模的減小而增加,而希拉里的支持率則相應降低。通過將2016年大選結果的縣級數據按照美國大都市區(qū)界定進行重組排列,可以發(fā)現特朗普相較希拉里以259比122贏得了更多數量的大都市區(qū)選民的支持,但在選票份額方面卻以44%比51%輸給了希拉里。這主要是由于兩位候選人所贏得的都市區(qū)在人口規(guī)模上存在顯著差異。在人口為100萬人及以上的大都市區(qū)內,希拉里以56%對40%的得票率占據絕對優(yōu)勢,但是在人口規(guī)模減小到50萬至100萬人時,特朗普的得票率就增加至48%,并領先希拉里兩個百分點。相應地,隨著都市區(qū)的人口規(guī)模繼續(xù)縮小到25萬至50萬人和25萬人以下時,特朗普的得票率隨之分別遞增至52%和57%。
大選結果在城市規(guī)模方面的分化本質上所反映的仍然是經濟差異的影響。支持希拉里的主要是人口集中和經濟富裕的發(fā)達城市。以具體的大都市區(qū)為例,希拉里在由高科技產業(yè)集聚的舊金山-奧克蘭-海沃德(SanFrancisco Oakland Hayward , CA)和圣何塞-桑尼維爾-圣克拉拉(SanJose Sunnyvale Snata Clara,CA)兩個大都市區(qū)分別獲得了76.7%和72.9%的高額選票,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邁阿密、費城、波士頓、西雅圖等美國排名前幾大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區(qū)內也都獲得了60%以上的選票。與之相對,特朗普所贏得的大都市區(qū)多數仍以傳統(tǒng)制造業(yè)為主且工人階級比例較高,這些都市區(qū)更容易受到制造業(yè)衰退的影響。例如,位于“鐵銹帶”的辛辛那提都市區(qū)(Cincinnati, OH-KY-IN)、印第安納波利斯-卡梅爾-安德森都市區(qū)(Indianapolis Carmel Anderson,IN)和匹茲堡都市區(qū)(Pittsburgh,PA)。特朗普在不同規(guī)模城市間的得票情況符合假說三。
結論
特朗普當選以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不僅對美國政治的走向帶來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世界政治秩序也造成了劇烈沖擊。本文的分析表明,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的勝利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其背后蘊含著全球化進程中美國社會分化與政治極化的深刻機理。本文通過對美國大選的選舉地理分析,探究了全球化導致美國當前右翼民粹主義強勢抬頭的原因。本文基于美國經濟地理的三組區(qū)域分化,結合美國參與國際貿易的要素稟賦推導出貿易政策偏好的三種區(qū)域分化形式,然后根據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主張,針對他在不同區(qū)域的支持率提出一組可檢驗的假說,最后利用2016年美國大選數據對假說進行了驗證。對特朗普的主要選民基礎的區(qū)域性分析,有助于人們理解特朗普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及當前美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微觀動因。
簡言之,全球化構成了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根源。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斷加深的經濟全球化,在推動美國成為全球金融中心與科技霸主的同時,也加深了美國內部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作為美國稀缺要素的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在全球化進程下日益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失利者,他們所集聚的區(qū)域——中西部的“鐵銹帶”、遠離城市的農村、小規(guī)模城市——也相應地面臨著嚴重的制造業(yè)衰退、收入下降及失業(yè)問題。在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憑借旗幟鮮明的反全球化主張和極具感染力的反建制言論,有效地迎合了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經濟利益訴求,從而夯實并擴大了他在上述區(qū)域的選民基礎。
自2017年執(zhí)政以來,特朗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以“美國優(yōu)先”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例如,加強基礎設施投資、鼓勵產業(yè)回遷、大規(guī)模減稅、反對多邊貿易協(xié)定、施加高額關稅、打擊非法移民等,旨在“為全球化浪潮中受挫的藍領階層兌現承諾”。盡管如此,由于政策的落地程度不一、短期化傾向突出以及受到國外的批評和反對等,上述政策的實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大打折扣。特朗普就任以來,美國傳統(tǒng)制造業(yè)及其分布區(qū)域的長期衰退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性逆轉。2020年美國大選即將來臨,特朗普能否連任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僅就經濟因素而言,美國經濟地理的總體分布情況并未發(fā)生重大變化。因此,特朗普要想在2020年大選中保住藍領中下層選民的選票,仍然需要重點關注中西部“鐵銹帶”、遠離城市的郊區(qū)與農村、小規(guī)模城市這些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聚集區(qū)域。不過,無論最終選舉結果如何,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政治思潮都將繼續(xù)影響未來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調整與轉向。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